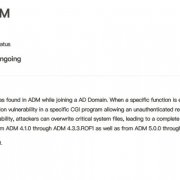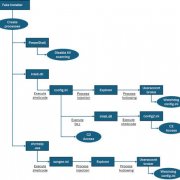成長所歷經的社會,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小時候,總統不能直選,報紙張數有限制,有些民代不用選卻可以一直做下去。在我小時候,中學男生得理平頭,上學穿軍訓服、戴大盤帽,老師體罰學生不會引起什麼爭議。在我小時候,當然已經很少人結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選填大學、就業抉擇完全聽父母的,還不在少數。
我們的社會所歷經的改變,一般被稱之為「民主化」的歷程,這樣的民主化,比多數人理解的來得更廣泛、更全面。我們通常只想到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較少體會到學校與家庭同樣歷經了民主化的過程。現在在校園裡,下課會有學生來找我,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師,我從開學到現在,這是第一次來上課,你看這要怎麼辦比較好?」這在我念大學的年代,是無從想像的一種場景。
這樣的改變有好有壞,好處是,我們的學生不再輕易服從單一權威,社會比較可能有多元的發展。但是我們這樣的社會所造就出來的新一代,習慣於以自己既有的標準來衡量一切──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也就對於任何己身之外的、與自己的習慣不合的社會體制,越來越沒有耐心、沒有容忍度。
當我們的學生還在學校、家庭裡的時候,這些問題都不大,最多就是老師、家長們發發牢騷而已,容忍學生、小孩的「多元性」,被認為是當代老師與家長的天職。真正的問題,會是在年輕人投入職場以後。我們的社會民主了,學校民主了,家庭民主了,但是從來沒有人要求企業也得民主。對現代的年輕學子來說,進入職場,等於是從一個高度民主的成長環境,投身威權的「鐵幕」,適應不良根本是常態而非特例。臺灣的草莓族現象,中國的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在我看來都與這樣的社會體制斷裂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中國並不是一個政治民主的國家。
對跟我差不多同年紀,乃至更年長一輩的工作者來說,我們是在沒那麼民主的社會、學校氛圍中長大的一代,面對企業組織的威權體制,相對來說,也就沒有那麼敏感而容易受傷。現代的年輕人,面對的卻是一個民主三缺一的社會體制,二十二歲之前,不管是在社會、學校或家裡,只要我喜歡,通通都可以,二十二歲以後,卻是樣樣得聽別人,有一套嚴格的組織規範得遵守。某種程度來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分裂症。
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1976年提出「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的概念,他主要是說,資本主義要求一個當代人在工作場域嚴守理性與紀律,扮演消費者角色時又期待我們縱慾狂歡,在文化上是既斷裂又矛盾的。30多年後的今天,在我看來,工作場域與學校、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的民主文化落差才是最大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企業可以民主嗎?這是迄今沒有人可以回答,或是敢於回答的問題。
專欄作者
熱門新聞
2026-02-06
2026-02-09
2026-02-06
2026-02-06
2026-02-06
2026-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