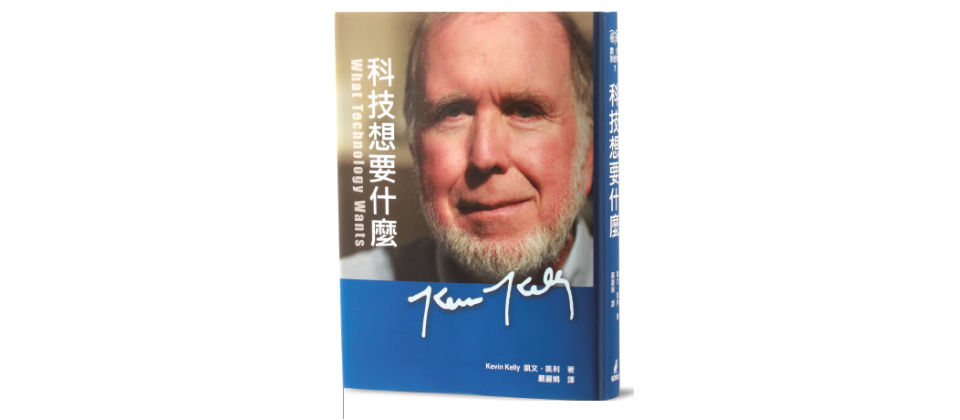
科技想要什麼?科技想要的東西跟我們一樣──那一長串人類渴望的優點。科技發現了自身在世界上最理想的角色後,就變成活性劑,為其他的科技提供更多的選項、選擇和可能性。我們的工作就是要鼓勵新發明物朝著這與生俱來的好處發展,和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我們在科技體中的選擇很真實、很重要,就是要引導我們創造出來的東西變成正向的模樣展現出來,儘量放大科技的益處,防止科技自我阻撓。
起碼在當下這個時刻,我們身為人類的目標就是要耐心引領科技走向原本就該走的方向。
但我們怎麼知道科技要往哪裡去?如果科技體的某些層面早已命定,某些層面則取決於我們的選擇,我們怎麼分辨這些層面呢?系統理論家斯瑪特建議,我們需要科技版的「寧靜禱文」。參與十二步驟打破成癮方案的人常念誦這篇據說於一九三○年代由神學家尼布爾寫成的禱文,內文如下:
主啊!求祢賜我寧靜的心,去接納我不能改變的事物;
賜我無限勇氣,去改變我有能力改變的東西;
並賜我智慧去認清兩者的差異。
那麼,我們怎麼得到智慧去分辨科技發展必然的階段和取決於人類意志的形式兩者之間的差異?要用什麼技巧才能凸顯必然的結果?
我認為能察覺到科技體的長期宇宙軌道,就有了恰當的工具。科技體想要演化創造的成果。不論哪個方向,科技都會延伸演化走了四十億年的路。從演化來看科技,我們可以看見這些宏觀的規則如何在眼前展現出來。也就是說,科技必然的形式會聯合起所有十幾種反熵系統(包括生命在內)共有的動力。(註:熵是一種簡單的科學名稱,表示荒蕪、混亂和失序。反熵就等於科技術語中的負熵,在本書中,反熵比單單減少混亂更令人振奮。可以把反熵想成獨立存在的力量,從一連串不太可能的實體向前猛衝。)
我認為,在科技的某種形式中觀察到愈多反熵特質,必然性和同樂性就愈高。舉例來說,比較使用蔬菜油蒸氣動力的汽車,和使用稀有地球金屬的太陽能電動車,可以檢驗兩種機械表現形式對這些趨勢的支持程度有多高,亦即不僅止於跟隨趨勢,還要加以延伸。科技和反熵力量的軌道貼近的程度變成「寧靜禱文」的篩選條件。
反熵
照我推論,科技想要的跟生命一樣:
更有效率
更多機會
更高的曝光率
更高的複雜度
更多樣化
更特化
更加無所不在
更高的自由度
更強的共生主義
更美好
更有知覺能力
更有結構
更強的演化能力
這串反熵趨勢可以當成檢查清單,幫我們評估新科技和預測它們的未來發展。我們可以用這份清單引導我們來引領科技。比方說,邁入二十一世紀時,科技體進入獨特的階段,我們建造了很多精細複雜的通訊系統。要在全球接線有好幾種方法,但我的預測很謹慎,最能持續下去的科技做法是傾向能最大幅度增加多樣性、知覺能力、機會、共生主義、普及程度的表現方法。我們可以比較兩種互相競爭的科技,看哪一種有利於比較多的反熵特質。會開啟多樣性,還是加以關閉?指望能增加機會,還是假設機會愈來愈少?是否能增加內在的知覺能力,或完全忽略?普及度會成為助力,還是毀滅的力量?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或許可以問:大規模使用石油的農業必然會出現嗎?拖拉機、肥料、育種、種子生產商和食品加工商組成高度機械化的系統,提供豐富的便宜食物,奠定根基讓我們有閒暇去發明其他的東西。人類因此愈來愈長壽,更有時間來發明,最後食物系統也增加了人口,進而產生了更多新的想法。這個系統對科技體軌道的支持程度是否超越了之前的食品生產體制,也就是生存農業和畜力混合農業達到高峰的時候?我們或許會發明另類的食品系統,相較之下又如何?一開始粗略地說,機械化農業一定會出現,因為能夠增加不少優點,例如能源效率、複雜度、機會、結構、知覺能力和專業化。然而,多樣性和美感卻沒有增加。
根據許多食品專家的說法,目前的食品生產系統高度仰賴少數幾種主要農作物(全世界只有五種)的單種栽培技術(不夠多樣化),因此需要用病理方式加以干預,使用藥物、殺蟲劑和除草劑,還有土壤翻動(減少機會),也會過度依賴便宜的石油燃料來提供能源和營養物(降低自由度)。
其他規模擴及全球的情境則很難想像,但從一些蛛絲馬跡可以看出,比較沒那麼仰賴政府津貼或石油或單種栽培技術的分散型農業或許能行得通。演化出來的超在地化專業農場系統或許會雇用真正在全球各地移動的移民勞工或機警靈巧的機器人勞工。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在高科技的量產農場中看到科技體,而是在高科技的個人或地區農場上。和愛荷華州種植玉米那一帶的工廠化農場相比,這種先進的園藝更能帶來多樣性、更多的機會、更高的複雜度、更有結構、更加專業、更多選擇和更強的知覺能力。
同樂程度更高的新農業會「領先」工業農業,就跟工業農業超越自給式農業一樣,後者仍是目前大多數農夫的生產模式(大多數農夫住在發展中國家)。利用石油的農業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必然還是全球最大的食物製造來源。科技體的軌道指向更有感情、更多樣化的農業,巧妙地把科技體包覆起來,就像大腦內負責語言技能的一小塊區域控制了我們的一大塊動物腦。如此一來,農業一定會變得更多元化、更分散。
科技有其必然性,即使被刻意阻擋,能量總有釋放的一天
但如果科技體的軌道是由一長串必然性組成,為何我們需要費神去激發這些必然性?不會自發展現出來嗎?事實上,如果這些趨勢必然會出現,我們費盡全力也無法遏止,不是嗎?
我們的選擇可以減緩必然性的速度,想辦法拖延,想辦法阻擋。正如北韓黑暗的天空所示,選擇避開必然性絕對沒問題,但無法永久。另一方面,也有幾個不錯的原因要我們加快必然性的腳步。想一想,要是一千年前的人接受了地方自治、大規模都市化、女性受教育或自動化的必然性,現在的世界會變得多不一樣?提早接納這些軌道,很有可能加快了啟蒙運動和科學的到來,讓數百萬人脫離貧窮,幾個世紀前的人就得享長壽。反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時期,這些運動受到抗拒、延後或積極鎮壓。而抗拒、鎮壓的結果,成功創造出缺乏這些「必然性」的社會。從身在系統內部的人的角度來看,這些趨勢似乎並非必然。但從後來的時空往前回顧,我們同意,它們顯然是長期的趨勢。
長期的趨勢當然不等於必然性。有些人認為,這些特殊的趨勢到了未來仍不是「必然的」,黑暗時代隨時可能出現,扭轉這些趨勢。也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能夠歷久不衰,才會變成必然。這些傾向並非注定在某個時刻出現。應該說這些軌道就像重力對水的引力。水「想要」從水壩底部漏出來。水分子一直在想辦法流下去跟漏出去,彷彿著了魔般無法自拔。就某種意義來說,即使被水壩阻擋了數個世紀,總有一天一定會漏出來。
科技的規則並非暴君,不會要求我們古板守舊。必然發生的事也不是排好時間表的預言,比較像是牆後面的水,鬱積了一股無比強大的衝力,等待被釋放的時刻。
或許讀者會覺得我描繪的超自然力量,類似在宇宙中漫步的神靈,但事實上幾乎相反。這股超自然力量跟重力一樣,融入了物質和能量的構造。跟隨物理學的走向,遵守熵的終極定律。這股力量等著爆發到科技體的科技產物中,最早的動力來自反熵,藉由自我組織慢慢累積,逐漸從無生命的世界投射到生命中,再從生命投射到心智,再從心智投射到心智的創造。在資訊、物質和能量交錯之際,就能看到這股力量,雖然最近才有人考察,仍可以重現和測量。
在接下來的小節內,我會簡短描述十種推動我們前進的普遍傾向。
共生主義
在地球上,有一半以上的生物都屬寄生生物。也就是說,在生命中至少有一個階段要靠其他物種才能生存。同時,生物學家相信每種現存的生物(包括寄生蟲在內)也是至少一種生物的宿主。因此自然世界也是共同經驗的溫床。
在連續的共生主義中,寄生狀態只是其中一個程度。在連續體的一端,所有的生物都要靠其他生物(直接依賴父代,間接依賴其他物種)才能生存,在另一端,藻類和菌類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共棲共生,組成地衣這種共生體。在兩端之間則有不同類型的寄生狀態,有些完全不會傷害宿主,有些寄生生物則會協助宿主。
演化(或許說共同演化比較恰當)過程中織入了三股愈來愈強的共生主義:
一、生物在演化過程中愈來愈依賴其他生物。最古老的細菌靠著沒有生命的岩石、水和火山煙來維持生活;只會接觸到不會動的物質。之後,如大腸桿菌般更複雜的微生物一生都住在我們的腸子裡,周圍是人的活細胞,吃我們的食物。它們只接觸到其他的生物。過了一段時間後,生物發源的環境比較有可能充滿生氣,不會死氣沉沉。整個動物王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趨勢。要是可以從其他生物身上偷來食物,何苦要從元素中自行製造呢?
二、在生物演化時,大自然創造出更多機會讓物種之間彼此依賴。每個為自己創造出成功利基的生物也會為其他物種創造出有潛能的利基(都有可能進入寄生狀態!)。
三、在生物演化時,同一物種的成員彼此合作的機會提高了。生物間的群居性提高,為演化提供穩定的機制。一旦社會化出現,就不太可能走回頭路。
人類生活浸潤在所有三種共生主義中。第一,我們的生存極度仰賴其他的生物。我們吃植物和其他的動物。第二,地球上沒有其他物種像人類這樣大量運用其他種類的生物來保持健康和繁盛。第三,人類是出名的社交動物,需要其他人來扶養我們長大、告訴我們如何生存和保持清楚的頭腦。因此,我們的生活共生程度極高,深入其他的生物。科技體把這三種共生主義又向前推了一步。
今日大多數的機器不會碰到地球,或不碰到水,甚至不接觸空氣。在我寫下這些字的時候,個人電腦核心中跳動的微電路心臟與元素隔絕,周圍全是其他的人工製品。這微小的人造物靠著巨大渦輪(天氣好的時候,則是屋頂上的太陽能板)產生的能量生存,把輸出送到另一台機器(我的電腦螢幕),要是幸運的話,等它的壽命結束,珍貴的元素還可以由其他機器吸收。
有很多機械零件從來不接觸我們的雙手。由機器人製造,塞入裝置(例如汽車裡的水幫浦),然後放入更大的科技發明物裡。不久以前,我跟兒子拆解了一台很老的CD播放機。當我們打開雷射盒時,我相信我們是首先看到那精細內部零件的非技術人士。之前播放機的內部只被機器碰過。
科技體朝著人類和機器共生程度愈來愈高的方向移動。這個主題很適合拍成令人熱血沸騰的好萊塢科幻鉅作,但在真實生活中也能在上百萬個小地方見證。大家都看得到,現在我們正用網路和 Google 一類的科技創造共同的回憶。當Google(或其他衍生物)能夠了解口語的問題,寄居在人類的衣物上,我們就能把這項工具快速吸收到腦海裡。我們會依賴這樣的工具,工具也依賴我們,生存下去並變得更聰明,因為用的人愈多,工具的聰明程度愈高。
合作
有些人覺得這種科技共生很可怕,甚至到了駭人的地步,但跟使用紙張和鉛筆來做長除並沒有什麼兩樣。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沒有科技,就無法做長數目的除法。我們的大腦接線天生無法成就這項工作。我們用書寫和算數技法來乘除或處理很大或很多的數字。可以在腦子裡計算,但我們會把問題用虛擬方法寫在腦海裡的虛擬紙張上。我妻子小時候會用算盤來算數。算盤是四千年前發明的類比式計算機,這種科技輔助工具計算的速度比紙筆還快。要是沒有算盤,她會用同樣的方法,用手指撥弄虛擬的算珠來找出答案。有時候,完全仰賴科技來加減數字並不會讓我們覺得恐懼,但要仰賴網路來記得事情有時候就會讓我們覺得很糟糕。
科技體也提高了機器間的共生主義。世界上的電信流量大多不是人類彼此傳遞的訊息,而是機器之間的通訊。世界上的非太陽能(也就是透過科技方法創造的能量,在科技體的管線間流動),幾乎有百分之七十五用於移動、儲藏和維護機器。大多數卡車、火車和飛機用於貨運而不是客運。大多數冷暖空調不是給人類使用,而是給其他東西。科技體只有四分之一的能量用在人類的食衣住行上,其餘由科技創造的能量則用於科技。
科技體與人類之間共生程度增加的旅程才剛開始。就跟用紙筆做加法一樣,要熟悉這種共生狀態,需要透過教育。反熵趨勢朝著共生主義前進,最明顯的地方就是科技體提高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性。我想加以描繪,因為這條軌道馬上就要出現了。在接下來的十到二十年間,科技體的社會面向會變成最主要的特質,也是人類文化的重大事件。
人與人愈來愈緊密,也是自然的進展。一群人一開始的時候只是分享想法、工具、創作,然後進步到合作、協力,最後達到集體主義。每走一步,協調度便跟著增加。
在今天,網路上的群眾分享意願非常高。臉書和MySpace 上張貼的個人照片已經到達天文數字。可以說用數位相機拍攝的照片幾乎都會用某種方法分享。維基百科也很值得注意,它是個共生科技的好例子;而且不只維基百科,其他的維基網站也一樣。現在其他的維基高達一百四十五種,每種都驅動無數的網站,讓使用者可以共同寫作和編輯。網路上也能發表狀態更新、地圖位置和不完整的想法。此外,每個月光在美國,發表在 YouTube 上的影片就高達六十億,有相同興趣的人發表在同人小說網站上的故事則有數百萬個。分享組織的名單長到無法勝數:Yelp 的評論、Loopt 的位置和 Delicious 的書籤。
分享奠定了基礎,接下來就能晉升到社群參與的下一個層次:合作。當眾人一起朝著大規模的目標努力,群體的力量會產生群體的結果。業餘人士在 Flickr 上分享的照片超過三十億張,此外大家還協力標注了類別、標籤和關鍵字。社群裡的其他人把照片揀選成集。創用CC授權條款大受歡迎,表示在社群上(並非徹底的共產主義)你的照片就是我的照片。大家都可以使用照片,就像公社成員可以使用社裡的手推車。
團體總和的表現比組成部分更好
演化把共生主義設計在生物學中,因為共生主義的好處帶來雙贏的結果。個人得益,團體也得益。今日的數位科技也在數個層次上出現了同樣的效應。首先,在臉書和Flickr等聚合網站中的社交媒體工具直接帶給使用者好處,他們可以設標籤、書籤、分享等,把自己的資料歸檔好方便取用。他們花時間分類自己的照片,就能更方便地找到舊照片;這是個人得益。第二,個人的標籤、書籤和其他東西或許能方便其他使用者;一人的努力讓其他人使用影像時更不必費力。因此,個人得益時,整個群體同時得益。有了更先進的科技,群體共同的努力會出現額外的價值。比方說,許多遊客在同一個旅遊場景從不同的角度拍照,把所有的相片標記下來,或許能組合成令人讚嘆的立體成像。光靠一個人或許做不到。
貢獻給社群新聞網站的認真業餘作家帶來的價值遠超過個人的獲益,但他們會繼續貢獻,一個理由是這些合作工具散發出來的文化力量。投稿人的影響遠遠超過個人的投票,社群的集體影響力並非按著投稿人的數目成比例增加。那就是社會組織的重點,總和的表現比組成部分更好。科技醞釀的力量就在這裡,即將浮現。
額外的技術創新可以讓為了特定目的而合作的過程增長為一種慎重的協力合作。看看那數百種自由軟體計畫,例如維基百科。在努力的過程中,經過微調的社群工具協調了成千上萬成員的工作,帶來高品質的產品。一項研究估計,Fedora Linux 9 軟體發行前,總共耗費了一個人六萬年的工作時間。全球各地約有四十六萬人目前參與了四十三萬項自由軟體計畫,數字非常驚人。人數幾乎是通用汽車公司員工數目的兩倍,但沒有主管。協作科技的成效太好,許多合作的人從未碰面,或許來自很遙遠的國家。
科技體中的共生主義趨勢讓我們朝著古老的夢想邁進:儘量抬升個人自主和群體工作的力量。誰會相信貧困的農夫能從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處借到一百美元的貸款,然後還錢?那就是 Kiva 這個網站的用途,利用網際網路社群網站的共生主義科技,讓陌生人可以互相借款。每個公共健康照護專家都很有自信地宣稱,分享照片沒問題,但沒有人肯分享病歷。但在 PatientsLikeMe 這個網站上,父母把治療結果聚合在一起,提升自己的照護品質,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戰勝醫生和個人的恐懼。愈來愈多人習慣分享想法(推特)、在讀什麼書(StumbleUpon 推薦引擎)、財務(Wesabe 記帳網站)、所有一切(網路),已經變成科技體的基礎。
協調不是新的概念,但有一度很難讓全體一起執行。合作不是新的概念,但很難到達數百萬人的規模。有了人類之後就有分享,但陌生人很難彼此分享。共生主義不斷提高,從生物學延伸到科技體,指出另一波社交性以及社會主義即將現身。現在我們用科技來協力打造百科全書、通訊社、影片檔案和軟體,參與者遍布五大洲。橋梁、大學和特設城市也能用同樣的方法建造嗎?
在上一個世紀,每天都有人問,自由市場有什麼做不到?我們列下長長一串問題,似乎需要理性規畫或父權政府來解決,而不是運用市場邏輯驚人有力的發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場解決方案的效果顯然更好。把市場力量釋放到科技體中,造就了近幾十年來的繁榮。
現在我們想用同樣的方法來運用近來浮現的協力科技,用這些技術來滿足愈來愈多的願望,或許也能處理自由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好看看這些科技是否有效。我們問自己,科技共生主義有什麼做不到?到目前為止,結果令人吃驚。幾乎在每個轉折點,社交化的力量(分享、合作、協力、開放性和透明度)都證明了實用度超過大家的想像。每一次的嘗試,都讓我們發現共生主義的力量比我們想像的更強大。每次重新發明某樣東西,就會提高其共生程度。(摘錄整理自第13章)
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
凱文.凱利(Kevin Kelly)/著;嚴麗娟/譯
貓頭鷹出版
售價:480元
《作者簡介》
凱文.凱利(Kevin Kelly)
凱文.凱利(KK)是過去二十年來資訊科技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及報導先驅。一九九三年,他協助創辦了《連線》雜誌並擔任執行編輯至一九九九年。在其主導期間,該雜誌兩度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期間,KK曾擔任《全球概覽》的發行人及編輯。他過去曾召集首次駭客大會,並在一九八五年參與籌辦了網路線上服務先驅:The Well。
熱門新聞
2026-02-06
2026-02-09
2026-02-06
2026-02-09
2026-02-06
2026-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