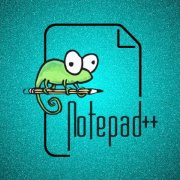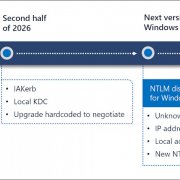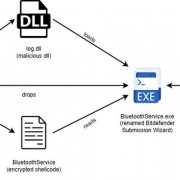|
艾西莫夫科普教室(上)(中)(下) Isaac Asimov/著 蔡承志、王原賢、葛茂豐/譯 貓頭鷹書房出版 售價:三本分別為399元 |
一九五七年,還遠在電腦的尺寸極度縮小,甚至可以裝在口袋裡之前,我曾經寫過一個故事,標題是「權力感」(The Feeling of Power),那個故事描述一個電腦極度普及的未來世界,那個時代的人已經忘了如何做算術——直到有一天,一位低階技術人員重新發現這項技術,並由於發表了9×7=63而震驚全世界。
我們果真有可能將一切都遺忘,達到這種程度?
依賴電腦的必然性
就某種程度而言,或許是吧;就讓我們想想,從前所發生的類似變革。
書寫發明之際,必然也會有許多人覺得,我們的記憶將就此踏上絕路,一旦人類有能力將思想與記錄寫下來之後,就會完全依賴在磚頭或紙草上做出記號,並會因此而變笨。
就某種程度而言,記憶的重要性確實降低,不過卻沒有消失,而如今又有誰會只為了讓人類鍛鍊記憶力,而放棄書寫(同時,在彼此記憶不符時,還要發生爭執)。
有誰會願意為了保存漂亮優雅的書法,而放棄印刷;或為了保有斯賓塞式書法,而放棄打字機;或只為了保存親友來訪的彬彬有禮教養,而放棄電話?
我們的確會由於這些技術進展而失去既有的事物,卻不會失去一切;我們的所得也會遠多於所失。
我們當然會依賴電腦,一旦失去電腦也會感到生存不易。事實上,我們也不需要遠眺未來。我們現在就已經在依賴電腦。失去電腦也會對我們造成問題。一旦所有的電腦停頓,主要產業都會無法營運,連表報文書都無法進行,更別提上千種產業政策的執行作業。
我們的武裝力量會完全陷入無助境地;科學研究會亂了分寸;最糟糕的是,政府本身也會癱瘓,光是國稅局就會立刻歇業。
對於電腦的依賴性——目前已經很高,同時還迅速提高——這是否是一場災難?或許不是。
我們甚至在電腦發明以前,就已經高度依賴於我們的社會中的各種複雜狀況。我們依賴縱橫各都市的完整電力輸送線路,及提供動力的發電機。我們依賴輸水管線,也依賴交通運輸設備運來食物送出垃圾,我們也依賴燃料與用來加熱的補給品,還有其他各種東西。
我們是可以降低依賴性,只要能夠將人類在過去數個世紀以來的所有進步完全還原。這樣一來,就可能會讓世界的四分之三人口消失,讓各都市萎縮成村莊,將所有產業複雜設施拆除,並成為一個農業星球——隨後我們還是要依賴馬匹、牛群與羊群等牲口的健康,還要依賴柴火供應及降雨量。
我們也無法自行回到過去。綜觀人類歷史,他們都會掌握任何機會,拋棄單純趨向複雜。人類會在有生之年,選擇性依賴可以提高舒適性,並豐富自己的生活的事物,如果背離這些事物,即使還能夠生存,生活卻會壓斷我們的脊背,耗損我們的軀體。
綜觀上述,世界還是會繼續往前邁進,並朝向電腦化大步前進。
沈迷於電腦世界的正面意義
一旦人群全心專注於電腦,無論是為了遊戲或紮實的教育,是否會形成社會疏離現象,我們是否會忘了如何與他人交往?
請記得,事情都有一體兩面。例如目前有數千人沈迷於「星艦影集」,這個影集已經開始成為他們的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他們也不會因此而產生疏離。反之,這部影集會驅使他們與其他具有相同興趣的人相互接觸,他們會組成影迷團體,舉辦影迷大會,等等。
簡言之,最初似乎會導致疏離的斥力,最後反而會形成促成人際交往的吸力。
與電腦玩遊戲,有可能驅使一個人去找其他人來測試自己的技巧;借助電腦來學習,也可能驅使一個人嘗試教育其他人。
想像一個世界,其中沒有任何兩個人所接受的電腦化教育是朝向完全一致的方向,也幾乎所有人都至少擁有某種類似宗教的狂熱。或許我們會出現一種空前未有的知性孕育現象。
為社會科學的知性發展帶來新的影響
人類知識一向是在解決各種單純問題的時候產生最大的進展。以天文學為例,我們多半將研究對象當成單一點,鑽研其在重力影響下的運動狀況,因此我們能以一種單純的方程式來進行敘述。就物理學而言,我們針對物體運動現象,及其他能量形態進行研究,也都能夠以相當單純的方程式來進行敘述。化學複雜度會比較高,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應付。
恆星、行星、撞球及原子的運動都具有高度單純性,研究物理學的人因而能獲得相當不錯的成果。
那麼,鑽研複雜系統的人又當如何?專事研究生物組織中分子的複雜行為,與生物演化及生物在社會結構中的行為的生物學家呢?還有心理學家還會更糟糕,因為他們必須處理人類的腦部,也就是我們所知最複雜的構造;還有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他們則必須處理人類社會,還要更深陷於其中。
也難怪,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表現似乎相當糟糕,社會進步也似乎是遠比不上技術進展,由於我們的社會還是維持原始的狀況,現代技術便有可能促使社會走上一條死路。
除非我們能夠擁有比進入電腦時代之前,更進步的工具來輔助我們的心靈,否則我們便無從改善這種狀況。
只要我們能夠發展出更好更先進的電腦,我們便有可能以空前速度解決空前複雜的問題。(這並不是說,所有問題都大體可以全盤解決,即使是使用最好的電腦也一樣。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產生近似解答,並可能得到足以解決當前問題的估計值。)
或許電腦也可以協助我們確定技術的副作用。有些表面上相當有用的技術變革,結果卻發生預期之外的副作用,並造成極大的損害,這是經常會發生的事例。灌溉所需的水壩,或許也會以其他方式,對該地區的生態造成無可避免的損害;某些施肥方式,卻有可能對土壤造成長期破壞。
這些事件不見得都很容易預測,不過,我們可以針對在全盤狀況中掌控各種不同事項的關連性進行研究了解,於是我們便可以運用電腦來進行模擬,並預測未來的狀況。
一旦我們提昇知識,改進程式,並使用能夠處理更多變數的電腦,產生的結果可信度便提高,用處也會更大。
時至今日,社會學還不是一門實證科學。實際上也不可能實現。我們不可能重新安排人類的社會(就好像我們對實驗室白老鼠的作為),施以各種壓力,記錄人類的各種反應,人類的喜與悲,生與死,並根據這些現象來獲得結論。人類社會太複雜了,人類的壽命太長了,我們也不能如此踐踏人權。
不過,我們可以在電腦電晶體網路中,採符號象徵方式來安排不同的社會。我們可以學會許多社會相關事項(借助於電腦),並了解如何建立假設與其中的關連性,隨後我們便可以讓電腦計算,並預測其方向路徑。
當然啦,我們也必然會想到,電腦化社會可以讓暴君學會如何更有效實施專制作為,電腦也可能促成對人性更長期的禁錮枷鎖。
我們無法保證不會發生這種現象。不過,或許電腦化社會也會顯示,專制君主最好不要太過於專制,才能延續較久;如果因此而促成更大的自由,或許自由還會繼續蔓延。
畢竟,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專制,即使沒有電腦,專制也已經延續如此久遠,我們也實在沒有理由害怕電腦會進一步促成專制。
我們也可以辯稱專制是由於害怕所引起。專制君主幾乎無視於社會運行方式,放眼四方只會看到危險與仇恨,他們會為了維護自己的支配與安全,向任意方向蠻橫地施以力量,並會愈收愈緊。
如果專制君主依循電腦化社會學的指引,至少他有可能會發現真正的危險源頭,同時他也只能選擇性施行專制統治。或許他還能了解,他的真正危險正是來自於自己的專制。
我並不保證必然會產生這種結果,不過這是一種可能性。由於始終都沒有其他有效的作法,也由於縱貫人類歷史,無論何時何處,自由與對人權的尊重幾乎都不曾彰顯,讓世界電腦化對我們也幾乎毫無損失,還有可能產生絕大的好處。
機器人與人類象徵兩種彼此互補的智慧
是否終有一天,我們能夠製造出機器人?我們是否有能力將電腦裝入頭顱大小的容器裡?
是的,當然啦,同時,以現代的技術而言,這樣的空間裡還可以納入相當精巧的電腦。
這種電腦是否能夠與人類電腦,也就是頭腦相提並論?
啊,那是不會的。目前甚至還沒有看到起點。即使簡單的電腦可以執行某些事情,例如:重複進行加減運算,執行速度與精確度也當然比人類頭腦快上數兆倍;然而,加減運算只是人類頭腦功能的極小部分。
然而,電腦在進行閱讀的時候會發生困難,還有,電腦也只能閱讀精確製作的電腦專用字母。反之,頭腦則可以輕易閱讀各種印刷與書寫字體,也幾乎不會由於字體不正確或拼音錯誤而延緩閱讀速度——同時,這也只是人類頭腦的極小部分功能。
人類頭腦擁有約一百億個神經元,或稱為神經細胞,或許還有高達九百億個輔助性細胞,這些細胞全都相互牽連形成極度複雜的模式,目前我們對此也還不明瞭。個別神經元,本身就遠比電腦裡的任何單元都更小,同時也不像是我們的微電晶體一樣,只是一種電源開關裝置,實際上,神經元是由極端複雜的龐雜分子組成,其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卻也有可能擁有極為強大的功能。
不過,如果電腦的功能彈性與複雜度穩定提昇,是否會變得具有相當智慧,並讓人倉皇失措?
是的,自然會如此。就我們所知,人類頭腦純粹是由物質、能量,與極度複雜的組織構成。倘若我們能夠以夠小的組件來製造電腦,並將這些組件構成足夠複雜的組織,理論上,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無法製造出能夠與人類智慧匹敵的東西(當然,我們也很難預測這要花多久的時間)。
同時,如果我們能夠製造出一部與人類一樣聰明的電腦,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製造出比人類更聰明的電腦?
的確,為什麼不行?或許這就是演化的功能。在超過三十億年時光裡,經過嘗試錯誤的發展過程,原子與分子終於在極其緩慢的改進過程裡,組織形成了一個擁有充分智慧的物種,並能夠在幾個世紀,或甚至幾十年光陰裡,踏出新的一步。隨後並開展了一個全新局面。
人類是否會拒絕發明出一種智慧超越本身的東西?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真的有選擇的餘地嗎?
如果電腦變得比人類更為聰明,它們是否會取代我們?
或許不會。電腦是透過異於頭腦的方向,藉著不同步驟,由完全不同的組件,及根據不同的理由發展出智慧。就算電腦的智慧能夠凌駕我們,或許在其他各方面還是不如我們。
或許,人類與電腦這兩種智慧,彼此互補的情況會遠高於相互競爭,同時,彼此合作也能夠產生出遠比各自獨立所能發揮的更高功能。
一旦有那麼一天,在地球上萌芽的智慧,從誕生星球崛起,在銀河系的各個象限定居,到時或許會是由兩種智慧協力完成。同時,其中的資深夥伴,也就是人類頭腦,或許還是擁有這種夥伴關係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許到時候,這些也還沒有經過全盤了解或完全複製。(摘錄自上冊卷六)
《作者簡介》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
廿世紀三大科幻小說家之一,生於白俄羅斯,3歲時隨父母移民美國、定居紐約。聰明絕頂的他19歲就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接著獲得該校化學碩士與博士學位。1949年成為波士頓大學醫學院講師,擅長生動活潑、充滿機智與幽默、跨領域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喜愛,也啟發了許多優秀後進。1958年因為太熱中寫作,決定辭職,成為專業作家。1992年辭世為止,著作已經將近五百種,幾乎涵蓋科學與文化的所有領域,堪稱自由穿梭時光的科學哲人。
熱門新聞
2026-02-02
2026-02-03
2026-02-04
2026-02-02
2026-02-04
2026-02-03
2026-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