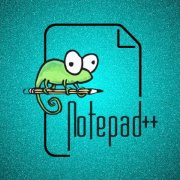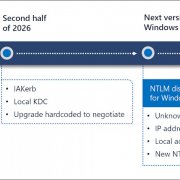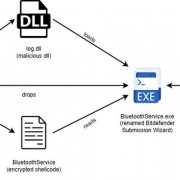這世界上不管是大公司與小公司,大人物與小人物,在工作及投資上常常面對一個基本問題:我該選擇「固定獲利」或「高風險高報酬」呢?當然聰明的人會做一個投資組合,將這兩者分配比例,形成積極成長型或者保本穩健型的策略。商場上面對這個問題似乎比起投資更複雜,因為投資可以逃走的速度比起企業想要逃命的速度快很多,企業一但在某個區域生根,要搬走並非短時間內的事情。再就風險來說,投資的話,可以停損;但企業很難,嚴重一點會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
Discovery頻道常說,自然界並非我們所看到那樣溫和,在我們周遭每天上演著數以百萬計「吃與被吃的」殘酷掙扎。英國石油(BP)曾經遇到一個問題:該在目前已經開採到原油的固定地區持續開採?還是到另外一個「有可能」鑽到石油的地方開採?因為鑽油的成本很高,因此大家習慣在已經鑽探到原油的位置開採,比較有把握。不過牛津大學的科學家有一項研究改變了這種觀念,他們研究椋鳥在捕食昆蟲的行為中發現,椋鳥不只會在固定可以抓到蟲子的地方捕食,也常常會冒著「被獵殺」的風險到別的陌生區域尋找蟲子。英國石油把這個行為應用到鑽油的思考上,五年產生了五億多美元的利潤。
椋鳥為什麼要冒死跑去別的地方捕食?牛津大學的研究員認為:「即使不能獲得最大收益,增進知識也有一定價值。」椋鳥有沒有想這麼多實在不知道,但顯然演化的力量,適者生存的結果中,這個行為扮演著關鍵性的因素。
越來越多的警訊告訴我們,臺商應該要轉往勞力更低廉的市場,或者必須提升產品價值,否則會被溫水煮青蛙,等到水沸騰了想要跳也來不及了。「報章雜誌的人不懂經營的辛苦啦!工廠怎麼可能說搬就搬?」在東莞經商的學長對此很不以為然,但是每天卻也一直抱怨「工資太高」「找不到工人」「流動率太高」「物價飛漲」……,由於環境的溫度是慢慢提高的,本來可以跳走的青蛙,固然覺得溫度變高了,但還是可以承受,等到發現出狀況時,就已經來不及了。「但是去越南或者印度考察不是我們想去就去,我們是跟隨著產業鏈移動的!」由於工廠有上下游群聚效應的現象,所以單單一個廠過去不行,需要整個肉粽都過去,但不見得大家都有共識。
看看椋鳥的例子,其實現在談去哪裡還太早,椋鳥冒著生命危險取得對於新環境的「知識」,得以在演化中生存,我們是否也該思考知識這回事呢?簡單講就是走走看看,先考察,了解新環境的條件,比較之後再來決定也不遲。
最近聽到一則報導,進入印度的外資之中,臺商排了倒數的名次,於是大家開始擔心,不進入印度會怎麼樣?過度投資中國會怎麼樣?臺商一向是全球製造大軍的前鋒,印度最缺的也就是製造業,我看過很多文章討論為何我們不容易在印度建立工廠。關於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在大陸與臺灣經商的朋友,答案都不太相同,原因是對於印度「缺乏了解」、「印度的英語很難聽懂!」、「不太容易找到可以信任的左右手」。因為臺商會習慣任用一兩個當地的可信賴的幹部來協助管理。「政商關係不知道該怎樣搞?」透過政商運作一向是商業的捷徑,中外皆然。「自己會的管理技巧不知道有沒有用?」臺商習慣互相交流管理技巧,但因為在印度成功案例不多,所以也就缺乏「撇步」密笈,導致大家不知道該怎樣作。不過有個長輩提到,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該怎樣教會他們製造這件事」。
或許,從歷史上看,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都可以順利地導入臺灣式製造,可是印度與中國自古以來交流就很少,我們沒有辦法去「揣摩」對方的思維邏輯,同樣的對方應該也認為我們不好懂吧?不過如果真的如同預期,2050年全世界國民生產毛額第一名為中國,第二名印度,第三名美國的話,我們現在確實可以採取跟椋鳥一樣的策略,多跑多看多了解,直到時機成熟為止。沒有人在催促我們要立刻搬到內地、越南、印度,但我們最好都能看一看,了解當地的產業架構,再來思考該怎樣切入。
每次走在中國大城市街頭,同行的朋友常常會說:「看,這地方當初我來的時候地價很便宜,現在已經漲到買不起,早知道我就……。」以前我都會陪著一起感嘆,但現在我會反問:「越南、印度這些國家機會才剛開始,你怎麼不會想去那邊試試看呢?」答案有很多種,但最多的一種是「沒辦法,我不熟,沒人帶路」。很有趣的是,我們有蠻多的華僑在東南亞,卻比較少聽說有華僑在印度,沒有華僑,就比較少人帶路,少了當地的嚮導,自然學習曲線與風險就高了。
變化的世局中,我們都算是正在被煮的青蛙,就缺少一個像椋鳥一樣的衝動,去冒一次險也好的好奇心。有所行動,到第一線去感受,多去幾次待久一點,我想以臺商的腦筋,很快就會有印度攻略密笈發行的。
專欄作者
熱門新聞
2026-02-02
2026-02-03
2026-02-04
2026-02-02
2026-02-04
2026-02-03
2026-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