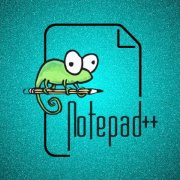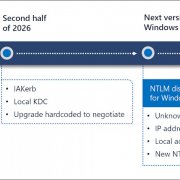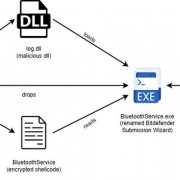應中央研究院之邀,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第一次來到臺灣,參加「大江健三郎文學學術研討會」。這本來應該是個很單純的文學、學術活動,卻因為有媒體踢爆,由於中國的干預,這項活動由原本的「國際會議」,降格為「兩岸會議」,而且原本規畫與會的作家李昂遭到排擠,因而成為敏感的「政治」事件。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曾表示,這個研討會一開始即定調為兩岸會議,沒有所謂中國強力干涉的問題。但另一方面,負責主辦該研討會的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明輝投書報刊指出,東京大學中文系原本有意合辦此項活動,但是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堅決反對之下而觸礁了。
翁啟惠、李明輝這兩位先生所說的,我相信都是真話。然而,令我感到好奇,而且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的問題是,探討一位「日本」作家的研討會,有「日本」東京大學願意主動協辦,而且還是我們最在乎的英國《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名第22的東京大學(咱們臺灣大學歷經千辛萬苦地擠入第95名,就叫我們高興的不得了了)。按照常理推斷,正常人豈不是應該樂於把兩岸會議「升格」為國際會議,讓這個學術會議得到更多資源、看起來更有模有樣?但是我們卻反其道而行,堅持要「維持」原有的兩岸會議格局。另外一項值得我們困惑的是,中國的一方,為何也不願意讓這項會議升格為「國際級」呢?
中國這一方的考量,李明輝先生的文章已經給了我們答案──中國認定臺灣不是一個國家,所以沒有資格辦「國際」會議。這是中國官方長期以來的一貫立場,不是針對這場會議而發難。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我們自己內部的政治偏向、文化氛圍與涉及中國事務時的態度。
說中研院屈從於中國的壓力,因而拒絕將兩岸會議升格為國際會議(不是立委或報紙所說的降格),我想這倒也未必。不過是一兩年前,當我被指派要協助籌辦一場學術研討會,主事者總是會提醒我,要在會議名稱加上「國際」兩個字,而且至少要有外國學者二到三名以上(中國地區的學者不在此列)。原因無他,政府為了要加強所謂的國際化,符合這樣格式的會議,才容易得到政府的補助。
在去年政黨輪替以後,顯然這樣的政策傾向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我的一位同事提醒我,現在學術會議要得到政府單位補助,加上「兩岸」二字要比「國際」有效得多。我大膽猜測,中研院堅持不願將兩岸「提升」到國際的層次,是不是也跟這樣的政治/學術趨向有關呢?
如果真是如此,我們就不得不為臺灣的發展走向感到憂心忡忡。當「兩岸」變得比「國際」還來得重要,這和只看自己肚臍眼的本土化政策沒什麼兩樣,都是目光短淺、只為政治服務的自我縮限。
中國的打壓並不可怕,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我們臺灣人心中,似乎都住著一個新警總。這樣的新警總,結合了政治與經濟的力量,比過去的「老」警總,更加幽微,因而也就更難加以防範與對抗,這對於我們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造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
專欄作者
熱門新聞
2026-02-02
2026-02-03
2026-02-04
2026-02-02
2026-02-04
2026-02-03
2026-02-05